我們看到每分每秒的想象力都僅僅關注于進行新一次的鑿擊,去揭示出那獨特的、被埋藏的雕像。——雅克·裡維特
你可以從這個“長廊”讀解出你想要看到的東西,佩雷并不像其他電影作者那麼吝啬至極到連些許微不足道的放權也不允許,隻想着完全占據影片的闡釋權,不僅如此,他還實際上十分歡迎閑逛“長廊”的遊覽者們各取所需。把其中有關佛朗哥政權統治下的電影審查與發行制度的介紹及批評視為一種參觀前免費贈予觀衆的藝術導覽,或者填字遊戲裡的提示字詞,而答案并不唯一。坦白講,在這個“長廊”中,佩雷隻是提供給了我們一條但并不代表唯一的放映/參觀路徑,途中如果能仔細觸摸圍成長廊筆直形狀的牆壁,幸運的話,就會發現這些牆壁不是嚴絲合縫的,而是存在着或顯而易見或不易發覺的縫隙;無論如何,隻要沿縫隙推動牆壁,我們不需花費太多氣力即可對長廊的構造按不同要求進行相應的獨特的改造,甚至偷偷私藏某一段相中的,能與我們個體的觀影神經産生連接的影像也在很大程度上會有意無意間就被佩雷——别忘了他才是“長廊”的實際策劃者——視而不見。
 ...
...不過,在你們正式進入“長廊”參觀之前,我想還是有必要再補充幾句。按照蒙太奇的傳統定義,兩個鏡頭之間的沖撞——可以來自其表意,但圖形、表象、體積、空間、照明、節奏、素材與取景、素材與其空間性、過程與其時間性等等元素的沖突同樣适用——可以催化出其含義辯證的飛躍(正、反、合題),也就是愛森斯坦那個為人所熟知的等式:1+1>2。
 ...
... ...
...可如果你們想要在《長廊》裡看到這種稱之為“蒙太奇”的東西,那麼很遺憾,這願望恐怕大概率會以落空結局。因為佩雷隻向我們展示了“蒙太奇”的殘骸——相對于諸如愛森斯坦的“屠牛”段落那樣擁有完整且清晰的隐喻表達的蒙太奇——亦即隻含有一半的“蒙太奇”,而另一半,同時也是(常被視作)至關重要的能夠暗示出隐喻的“本體”究竟為何的那一部分則被佩雷剔除出去,而且絲毫不帶任何猶豫。
 ...
...工人對位被宰之牛,帝國主義的血汗工廠對位血腥無情的屠宰場,一切都無法變得更加粗野了,但在你們即将看到的鮮雞屠宰場中,這種隐喻式的圖像(以及聲音,像索拉納斯在《燃火的時刻》裡的垂直蒙太奇調用起聲音與影像的對位關系,屠宰的影像實際上是圖解了畫外音裡關于歐美帝國主義是如何在拉丁美洲進行經濟與文化殖民的叙述)卻從未如觀衆所願地同屠宰影像一道交叉并置于銀幕之上,想要喚起一種明确的意識反映。如果我們依舊傾向于認為這屬于某種“隐喻”的範疇,我們也隻能将其與《一條安達魯狗》的那隻斷手、《亞特蘭大号》中的小貓、《動物之血》堆成小山狀的頭顱、史雲梅耶開鑿舊物體的方式以及《322檔案》或者《至關緊要的歲月》裡看似自在而存實則是以蒙太奇的魔術棒賦予其生命的一顆蘋果——這個序列還可以無限增加,但我想這些極具代表性的“适應電影本性的物質形态”(伊芙特·皮洛語)已經足夠向你們,“長廊”的參觀者們明示這一點——置放于電影的同一側。
除此之外,假使你們在這趟絕無僅有的“長廊”之旅前有幸獲得過進入《吸血鬼之日》幕後樂園的門票——《吸血鬼》——我想你們就應該會對佩雷的“壞品味”做足準備,但這種“壞品味”,在試圖架起表象與内裡溝通橋梁的超現實主義派裡找到影像淵源之餘,從B級恐怖電影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佩雷的同仁:羅梅羅。速度與運動這一對雙向推動的組合關系在二者這裡都被發展到了極緻,對于其影片來說,每個場景,每個段落總是匆匆收尾,寥寥勾勒幾筆即宣告完成。
 ...
... ...
...在這一特征上,我們很容易說,佩雷的風格(羅梅羅也一樣)就是“閱讀障礙症”的風格,是——像人們常常诘難“影像”的那樣——屬于一個還沒有耐心讀完整句的孩子的風格,他們瘋狂地翻動書本,一次描寫還沒結束,其目光可能就已經飄到後一句話——換句話說,還有另一異于我們普遍意義的“看”與“聽”的視聽層面的維度在運作——這樣“讀”下去一段細緻的描寫可能隻會有幾個單獨的名詞與形容詞奔入眼球,甚至浏覽的時候沒注意到紙張的粘合都是常态,那麼這些字詞間的空缺由什麼物質來填充呢?——想象力,豐富的想象力,孩童般天真的想象力,這就是為何他們皆不害怕片中象征性動作的被闡釋可能會破壞影片的統一性,盡管一方面,其影片似乎就未曾在乎過什麼所謂的“統一性”,鏡頭從一個角度的特寫跳到另一個,抛棄了深度,自然也從來不給觀衆一個完整全景的連續性印象;但另一方面,這種象征性動作的突發性與不可預測性不禁讓我們懷疑羅梅羅與佩雷是否很享受将其剝離開電影的身體再用膠水草草縫合一下的類似頑劣行徑,你可以扯開這些肌肉組織,如果不介意噴湧而出的鮮血濺滿衣物的話,盡可能去撕扯好了,沒人會責怪你的。如果你們不介意我再使用比喻的方式進行論述的話,那我會說存在一種精細的戲劇式的心理現實主義,亦即如巴贊所說,“(譬如左拉)分解現實,然後按照他們的世界觀和道德觀重新綜合現實”,羅梅羅與佩雷則是做同樣的事,但更不修邊幅,也更不在意“分解”後的“綜合”是否吻合原先的切割線。
 ...
...回到“長廊”。之所以佩雷做出如此選擇,取走“蒙太奇”的一肢一節,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再新穎的蒙太奇組合隻要能夠傳達清晰有效的信息、含義或情緒,從其出土之日——與觀者目光相觸的那一刻——起也無法避免遭受氧化,腐蝕,随時間推移其原先的耀人光澤漸次暗淡,從迷人的金色演變成腐朽不堪的青銅色澤,其原初野性的思維不斷腐化為陳詞濫調,終歸于博物館收藏的展品命運,當然,是被名為“電影史”的博物館收藏——或者說,扼殺,這個“體制的、文化的、意識形态的空間”隻可能如誇特雷梅爾·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所描述式的“将藝術作品從其文化語境和政治語境中移除出去”,從而達到竊取作品“靈韻”的目的。佩雷一定以自己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這一點,否則片中兩段在鳥類博物館的遊蕩又從何談起呢?雷乃和馬克告訴我們“雕像也會死亡”,顯然,電影及作為電影核心的蒙太奇也是一樣,而佩雷想要避免這樣的命運,即使采取一條略帶笨拙、混沌的路徑也無妨;但必須避免風格僅僅凝結而成單向同性的晶體,他希望這個已經摻雜了些雜質,形狀不再呈現出規則構造又不再純态的晶體每一面,每一處棱角,每一個方向都有獨屬于自己的性質,每一次放映亦正如同向其通電一般都能夠引起觀看群體相異的反應。
最後,祝你們參觀愉快。
 ...
...注:文中有關博物館的論述引自友鄰Waldeinsamkeit翻譯的《博物館中的戈達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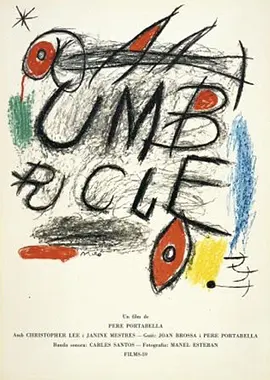

![[MIDE-742] 高橋聖子 2020 最新騎兵作品](https://upload-images.jianshu.io/upload_images/20131127-7d8d281d5f1cd953.jp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imageView2/1/w/300/h/240/forma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