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每分每秒的想象力都仅仅关注于进行新一次的凿击,去揭示出那独特的、被埋藏的雕像。——雅克·里维特
你可以从这个“长廊”读解出你想要看到的东西,佩雷并不像其他电影作者那么吝啬至极到连些许微不足道的放权也不允许,只想着完全占据影片的阐释权,不仅如此,他还实际上十分欢迎闲逛“长廊”的游览者们各取所需。把其中有关佛朗哥政权统治下的电影审查与发行制度的介绍及批评视为一种参观前免费赠予观众的艺术导览,或者填字游戏里的提示字词,而答案并不唯一。坦白讲,在这个“长廊”中,佩雷只是提供给了我们一条但并不代表唯一的放映/参观路径,途中如果能仔细触摸围成长廊笔直形状的墙壁,幸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墙壁不是严丝合缝的,而是存在着或显而易见或不易发觉的缝隙;无论如何,只要沿缝隙推动墙壁,我们不需花费太多气力即可对长廊的构造按不同要求进行相应的独特的改造,甚至偷偷私藏某一段相中的,能与我们个体的观影神经产生连接的影像也在很大程度上会有意无意间就被佩雷——别忘了他才是“长廊”的实际策划者——视而不见。
 ...
...不过,在你们正式进入“长廊”参观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再补充几句。按照蒙太奇的传统定义,两个镜头之间的冲撞——可以来自其表意,但图形、表象、体积、空间、照明、节奏、素材与取景、素材与其空间性、过程与其时间性等等元素的冲突同样适用——可以催化出其含义辩证的飞跃(正、反、合题),也就是爱森斯坦那个为人所熟知的等式:1+1>2。
 ...
... ...
...可如果你们想要在《长廊》里看到这种称之为“蒙太奇”的东西,那么很遗憾,这愿望恐怕大概率会以落空结局。因为佩雷只向我们展示了“蒙太奇”的残骸——相对于诸如爱森斯坦的“屠牛”段落那样拥有完整且清晰的隐喻表达的蒙太奇——亦即只含有一半的“蒙太奇”,而另一半,同时也是(常被视作)至关重要的能够暗示出隐喻的“本体”究竟为何的那一部分则被佩雷剔除出去,而且丝毫不带任何犹豫。
 ...
...工人对位被宰之牛,帝国主义的血汗工厂对位血腥无情的屠宰场,一切都无法变得更加粗野了,但在你们即将看到的鲜鸡屠宰场中,这种隐喻式的图像(以及声音,像索拉纳斯在《燃火的时刻》里的垂直蒙太奇调用起声音与影像的对位关系,屠宰的影像实际上是图解了画外音里关于欧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在拉丁美洲进行经济与文化殖民的叙述)却从未如观众所愿地同屠宰影像一道交叉并置于银幕之上,想要唤起一种明确的意识反映。如果我们依旧倾向于认为这属于某种“隐喻”的范畴,我们也只能将其与《一条安达鲁狗》的那只断手、《亚特兰大号》中的小猫、《动物之血》堆成小山状的头颅、史云梅耶开凿旧物体的方式以及《322档案》或者《至关紧要的岁月》里看似自在而存实则是以蒙太奇的魔术棒赋予其生命的一颗苹果——这个序列还可以无限增加,但我想这些极具代表性的“适应电影本性的物质形态”(伊芙特·皮洛语)已经足够向你们,“长廊”的参观者们明示这一点——置放于电影的同一侧。
除此之外,假使你们在这趟绝无仅有的“长廊”之旅前有幸获得过进入《吸血鬼之日》幕后乐园的门票——《吸血鬼》——我想你们就应该会对佩雷的“坏品味”做足准备,但这种“坏品味”,在试图架起表象与内里沟通桥梁的超现实主义派里找到影像渊源之余,从B级恐怖电影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佩雷的同仁:罗梅罗。速度与运动这一对双向推动的组合关系在二者这里都被发展到了极致,对于其影片来说,每个场景,每个段落总是匆匆收尾,寥寥勾勒几笔即宣告完成。
 ...
... ...
...在这一特征上,我们很容易说,佩雷的风格(罗梅罗也一样)就是“阅读障碍症”的风格,是——像人们常常诘难“影像”的那样——属于一个还没有耐心读完整句的孩子的风格,他们疯狂地翻动书本,一次描写还没结束,其目光可能就已经飘到后一句话——换句话说,还有另一异于我们普遍意义的“看”与“听”的视听层面的维度在运作——这样“读”下去一段细致的描写可能只会有几个单独的名词与形容词奔入眼球,甚至浏览的时候没注意到纸张的粘合都是常态,那么这些字词间的空缺由什么物质来填充呢?——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孩童般天真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何他们皆不害怕片中象征性动作的被阐释可能会破坏影片的统一性,尽管一方面,其影片似乎就未曾在乎过什么所谓的“统一性”,镜头从一个角度的特写跳到另一个,抛弃了深度,自然也从来不给观众一个完整全景的连续性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象征性动作的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不禁让我们怀疑罗梅罗与佩雷是否很享受将其剥离开电影的身体再用胶水草草缝合一下的类似顽劣行径,你可以扯开这些肌肉组织,如果不介意喷涌而出的鲜血溅满衣物的话,尽可能去撕扯好了,没人会责怪你的。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再使用比喻的方式进行论述的话,那我会说存在一种精细的戏剧式的心理现实主义,亦即如巴赞所说,“(譬如左拉)分解现实,然后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重新综合现实”,罗梅罗与佩雷则是做同样的事,但更不修边幅,也更不在意“分解”后的“综合”是否吻合原先的切割线。
 ...
...回到“长廊”。之所以佩雷做出如此选择,取走“蒙太奇”的一肢一节,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再新颖的蒙太奇组合只要能够传达清晰有效的信息、含义或情绪,从其出土之日——与观者目光相触的那一刻——起也无法避免遭受氧化,腐蚀,随时间推移其原先的耀人光泽渐次暗淡,从迷人的金色演变成腐朽不堪的青铜色泽,其原初野性的思维不断腐化为陈词滥调,终归于博物馆收藏的展品命运,当然,是被名为“电影史”的博物馆收藏——或者说,扼杀,这个“体制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空间”只可能如夸特雷梅尔·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所描述式的“将艺术作品从其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中移除出去”,从而达到窃取作品“灵韵”的目的。佩雷一定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一点,否则片中两段在鸟类博物馆的游荡又从何谈起呢?雷乃和马克告诉我们“雕像也会死亡”,显然,电影及作为电影核心的蒙太奇也是一样,而佩雷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即使采取一条略带笨拙、混沌的路径也无妨;但必须避免风格仅仅凝结而成单向同性的晶体,他希望这个已经掺杂了些杂质,形状不再呈现出规则构造又不再纯态的晶体每一面,每一处棱角,每一个方向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性质,每一次放映亦正如同向其通电一般都能够引起观看群体相异的反应。
最后,祝你们参观愉快。
 ...
...注:文中有关博物馆的论述引自友邻Waldeinsamkeit翻译的《博物馆中的戈达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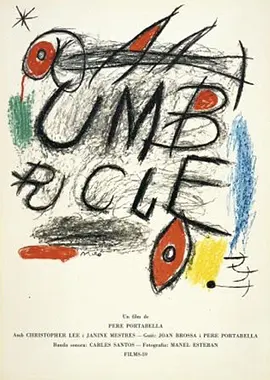

![[MIDE-742] 高桥圣子 2020 最新骑兵作品](https://upload-images.jianshu.io/upload_images/20131127-7d8d281d5f1cd953.jp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imageView2/1/w/300/h/240/forma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