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已獲得鈴木龍也導演本人授權//
申請授權時,有在郵件中跟導演說,如有需要将定期把中國觀衆的感想翻譯給他,所以大家看後要是很喜歡,或是有什麼想傳達給鈴木導演的話,請多多留下評論。
各位的反饋将會成為個人創作者很大的力量:D
 ...
...1 《無法的愛》(手機版)←請一定一定用手機等移動設備觀看!
【作品信息】
原名:無法の愛(Lawless Love)
導演・劇本・影像・剪輯・音樂・出品:鈴木龍也
制作年份:2022 | 時長:23min
聲優:巴山祐樹/小林香/KUREHA/彼方/富田大秀/大門嵩
翻譯&軸:雑食家
【故事梗概】
深夜。建築工地。
頭戴三角錐的男人和粉發女人,宿命般地走入對方的生命。
兩個社會邊緣人,跨越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愛與善惡之殇。
【獨立動畫短片 | 授權中字】社會邊緣人的愛與善惡之殇 | 鈴木龍也 *手機觀看将有奇迹?!_哔哩哔哩_bilibili
2 鈴木龍也導演 長文解說(近9000字)
發布日期:2022.12.04
原文鍊接:https://filmarks.com/movies/104841/reviews/141636480
翻譯:雑食家
我是《無法的愛》的作者鈴木。
作為一份獻給各位觀衆的場刊,
同時為了避免我自己在映後見面會上頭腦一片空白,
我将與這部作品有關的一切都記錄在此。
【制作原委】
2021年,我的拙作《MAHOROBA》在下北澤電影節上獲獎。下北澤tollywood的主管大槻先生是電影節的評審,他便邀請我在他的電影院上映這部電影。可由于電影時長過短,單獨上映存在困難。而那時,我正着手的MV《yoidore》即将收尾,就想着再做一部,三部作品合成一個動畫短片集上映。《無法的愛》就是由此開始制作的。2022年的新年剛過,我就開始推進,還自信滿滿地想着:“不過10分鐘左右的短篇,3月就能搞定~”然而,由于沒寫情節概要就開始制作,故事漸漸膨脹,成品最終超過20分鐘,成了我最長的一部作品,6月末才完成。10月底,《鈴木龍也短篇集 三個男人 MEAN ANIMATION》公開上映。tollywood的主管在此期間從未催促,讓我“随心所欲地創作”,我首先想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關于故事構想】
在前述的契機之下,當我開始構思創作内容時,我的自行車被偷了。我明明按規矩停在自行車停車場,也上了鎖,還是被一鍋端了。車是二手的BIANCHI(比安奇)牌,大約5萬日元買的,是自我來到東京後跟了我5年的愛車。我一頓好找。十字路口也好,夢裡也好,明明我知道它不可能會在那裡……當時我惱火至極,有好長一段時間,從車站往家走的時候,我總是疑神疑鬼地盯着那些從後方超越我的自行車。不過諷刺的是,徒步通勤使我有了更多思考的時間,由此冒出了不少點子。我最初隻是模糊地想了一個大概的故事線——“以自行車被偷拉開序幕,堕落毀滅式的男女愛情羅曼史”,以及“無法之愛”這個标題。另外一個點子,是我坐電車時想到的。
我不是很喜歡和别人靠得太近,所以就算有空位,也基本隻會站在門旁邊。這種時候,乘客們用手機看視頻的景象經常會映入我的眼簾。一般他們看YouTube和Netflix的時候用橫屏,看TikTok的時候會換豎屏。由此我靈光一閃——“以豎向畫幅開場的電影,在放映過程中變為橫向”。這樣的話在手機上看和去電影院看,就會收獲完全不同的視聽效果。我很希望能做出讓去電影院觀看的觀衆大吃一驚的效果。所以在創作之初,我就決定給這部作品設計2個版本,“手機版”和“影院版”。理由隻有一個:不論時代如何更叠,電影院才是電影的大本營。盡管我自己也會用手機看電影,但還是更喜歡去電影院,對在影院看的電影印象也會更深刻。如今,小劇場文化因流媒的興起和疫情逐漸式微,令人深感落寞。我想創作出一部有足夠沖擊力的作品,讓我自己以及觀衆們都能夠再次認識到在電影院看電影的宏大感。當然,這種設計非同尋常,處理不好極有可能破壞整部電影的水準。不過,我有一點堅信不疑的是,“這種設計至今還從未有人嘗試過”。不知怎的,隻要知曉這點,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人們看電影的理由有很多,而對于同時也在制作電影的我來說,“為了了解既存的手法”也是我看電影的理由之一。迄今為止,我在Filmarks(譯注:日本影評網站,同時也是鈴木導演發布這篇文章的網站)上記錄下了我看過的幾乎所有電影(近3000部),但沒有一部有“從豎屏到橫屏”的設計。其實我經常會這樣,每每當我發現這種“漏洞”時,我内心才終于對創作亮了綠燈。像我這種無名小卒…或者說,正因為我是個不受束縛的無名小卒,才應該去探索各種自由的元素,以及标新立異的表現形式。我内心暗自覺得那是自己肩負的義務,由此投身進入了影片制作環節。
【關于手法】
我不怎麼會畫畫,繪畫水平止步于在教科書上塗鴉的程度。所以在制作動畫上,我摸索出了一種獨屬于自己的手法,即“描摹GIF”。GIF在meme和LINE的表情包中很常見,是一種短時循環的圖片格式。制作動畫時,我會從中搜集素材,一張張分解,模仿其中的動作,按自己的風格畫圖,最後再将其串聯在一起。歸根結底,我的動畫就是無數“抄襲”的大集合,根本不值得任何誇贊,而且我到現在也不覺得自己的創作是從0起步的。不過說到底,我内心也會覺得“電影不就是這樣的嗎”……
在電影創作方面,我的手法也比較特立獨行。制作動畫時,我不會準備劇本和分鏡。僅敲定大緻内容後,就開始猛畫。完成一個鏡頭後,将其放到剪輯的時間線上,再找下個鏡頭,再畫,再連在一起。也就是拍攝真人電影時,“按順序拍攝”的手法。一般而言,動畫的制作應該都是在分工體系下推進,但我的電影完全是獨立制作,構想都在自己的大腦裡,也無需把劇本和分鏡拿去給誰确認。所以,如果要先“寫”劇本、“畫”分鏡,然後再着手“畫”正片,不僅累手還費時間,我才省去了這些步驟。(因為隻畫需要的鏡頭,到最後都不會有1張廢稿)
此外,在故事情節的創作上,我知道按我自己的性格,如果從頭到尾都完全根據既定計劃,按部就班地推進,肯定會感到厭倦,所以會比較即興地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推進故事。動畫和真人電影的不同在于,動畫缺少指揮活人時的那種不确定感。雖然反過來說,優點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縱角色,但“即興感缺缺”還是會令人感到有點索然無味。畢竟我想創作的是“戲劇”。所以我會嘗試像即興表演一般創作故事,摸索以往的動畫作品中不具備的“随意感”。說到底,我本來畫畫就畫得沒多好,用普通的創作手法肯定赢不了現有的作品,也對不起各位專業動畫師。所以最終還是覺得目前這種方法比較适合自己。而且就像《NEP League》(譯注:一檔以智力競賽為主題的日本綜藝節目)裡的礦車遊戲環節一樣,也有一道道闖關的快感。本以為要向右走的角色,不僅沒向左,反而出乎預料地飛上了天……盡管我才是創作者,在制作過程中卻有一種追趕角色的奇妙感受,因而我到最後都不感厭倦、盡興其中。
【關于參考作品】
剛剛花了挺長時間介紹電影的“外側”,接下來我會花更長的時間重點解說電影的内容部分。
首先來談談這部作品的主人公——隻野一男。一個由于擁有過于崇高的正義感,而被俗世錯誤理解的男人。這個角色的框架來自《木蘭花》(1999)和《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2019)中出場的警官和保安。就前者而言,我還引用了其片頭部分“我想要做善事…”的台詞,對角色的影響極大;而後者“夢想成為執法者的保安”這一設定和媒體暴力的描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頭戴錐形桶”的靈感來自千鳥(譯注:日本搞笑藝人組合)的大悟先生。我記得應該是《夜會》(譯注:日本綜藝節目)裡吧,在千鳥的經典外景“轉角裝傻”中,看到大悟先生戴着三角錐登場時,我猛然感到“就是這個了!”。這也是因為我在設計開頭部分時,有很明确的想法,不希望主人公在開篇就露臉,正好那個節點我又在摸索處理方式(實際上,直到隻野出獄後瞬間被撞那幕之前,隻野都沒有露臉)。這樣設計的理由倒是有幾個,不過最終還是因為我個人喜歡這樣。我直覺上覺得,像《野獸之死》(1980)和《白日焰火》(2014)那樣的叙事手法适合我這部電影,就這樣處理了。而且“看不見”,給人一種色氣滿滿的感覺,很有味道對吧。
而另一位主人公——愛,并沒有特别的原型。硬要說的話,前半部分“胡作非為的犯罪情侶”的形象構想來自《我心狂野》(1990)、《真實羅曼史》(1993)、《天生殺人狂》(1994),愛這個角色可能是無意識間将這些作品中的伴侶角色拼貼起來,由此誕生的一個形象吧。但其實我自己也不甚明了。我被問過幾次“您是不是喜歡她這樣的女性”,可哪有男人會喜歡開車撞自己的女性呢?所以其中并沒有我自己的投影。倒是一開始不知怎麼就覺得“發色選粉色比較不錯”,就此确定了電影整體的色調。自我畫出愛的臉的一瞬,我感覺我也像隻野一樣,整個人都被她帶着跑。
關于電影标題出現後,後半的故事情節,并非以特定的作品作為原型,而是基于某一事件創作的。我想看了電影的觀衆應該都發現了,就是2021年萬聖節那天發生的“京王線持刀傷人事件”。我還記得,當我在社交媒體上刷到現場視頻,看到“小醜男”傷人後,坐在車内顫抖着吸煙的模樣,我整個人都受到了巨大沖擊,心中湧起各種情感。其中既有對罪犯本人旁若無人的态度的憤怒,也因為自己經常坐京王線,萬一時間不湊巧……也有由于想象帶來的後怕。與此同時,也對身處“鐵籠”之外的安全區域、嘲笑似的拍攝“野獸”視頻的拍攝者,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異樣感。
我因為工作關系,會站在歌舞伎町的酒吧裡,聽不同的人講故事。畢竟是那樣一個地方,遇到的大多都是晚上工作的人。當時,有個年輕的男公關談起:“‘我’可是最強的欸。哎,最近應該經常會聽到吧?所謂的‘無敵之人’,那些制造無差别殺人事件的家夥。我覺得我能懂他們的心情。就那種覺得世上一切都無關緊要,我死了之後的事也都跟我沒關系……”和他一起來的男公關前輩已經爛醉,所以這個話題立馬變成了其他傻氣的内容,但我邊擦着玻璃杯,邊默默在内心反複思考着他留下的沉重話語。“小醜男事件”發生時,我猛地回想起男公關那天說的話,心情很難以言表。因為那個時候,我心裡也覺得我“懂”那個男公關的心情。我是由于自己很喜歡看電影,所以萌生了自己創作的想法,便開始着手制作,如今制作電影幾乎已經變成了我活在世上的證明。如果将“電影”從我的生命中抽走,基本就意味着我的“死亡”。對于時不時會陷入這類思考的我而言,無差别傷人事件的犯人絕非與自己毫不相幹。如今,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所思所想生存于世,無比自由的同時,又是一個痛苦且困難重重的時代。如果坐到了那班電車…如果沒有電影…我們隻是恰巧得以回避了這些分歧,但事實上,我,不,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那名犯人。另外,目擊者上傳的視頻底下的留言——“犯人好像在京王線上哦。我太氣了,給了窗戶兩腳哈哈 給大家亂添什麼麻煩”——也讓我感到十分違和。我就想着把這些元素全部塞進這部作品中。動畫制作到中期階段,大概3月底時,我才終于覺得自己清晰抓住了這部作品的核心主題和整體感覺。一般而言,無差别傷人事件的犯人畫像,新聞報道隻會簡單帶過,所以我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在其中。而在遭遇這一幕前的種種,我則是借助娛樂的力量進行了描畫。這就是這樣一部電影。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Mr.Children的《タガタメ》(TAGATAME)這首歌。這是一首以日常情景——“迪卡普裡奧的成名作,我剛剛已經錄下來了”——開唱,最終延伸至世界問題,是一首極富力量感的歌曲。我這部《無法的愛》也沿襲了其特點,同樣以“長距離”為目标,從非日常、颠三倒四的犯罪情侶出發,最終将觀衆帶入近在咫尺的社會問題之中,以此動搖觀衆的情緒。“我想救的,是你啊”這句台詞,大家可以認為是我對各類事件深度思考後給出的答案之一。
另外還有一些對本作産生影響,抑或是起到參考的作品。畫風方面,我是看了《複活節菜單》(2021)這部短篇動畫後确定的方向。制作期間觀看《法蘭西特派》(2021)時,其中的動畫部分也給了我靈感。至于阿德裡安·托明(Adrian Tomine)的漫畫和插畫,我則是從中大膽地引用了許多。在這之外,漫畫家丹尼爾·克洛維斯(Daniel Clowes)、查爾斯·伯恩斯(Charles Burns)、望月峰太郎和兼子笃;動畫導演原惠一、今敏等人的元素,或多或少都有出現在電影中。按鏡頭說明得再細一些的話,從圓洞中越獄逃出的設計來自《逃獄9人組》(2003);揍警察那一幕來自《老男孩》(2003)或《困鬥99号囚室》(2017)。“與出人意料的人同行的男人獨白”,其語氣語調和台詞都參考了《在路上》(2012)。
*如果再有記起來的,我會繼續在這裡更新。
盡管我已經一一分享了這麼多幕後故事,但其實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歡把自己的作品解釋得那麼明白,我覺得這樣很遜,也覺得這種行為非常不入流。但這部作品比較特别,我覺得“自己必須記錄下來”。真的沒有想到,目前這部作品居然在所有投遞的電影節中,都獲得了某一獎項,讓我很是摸不着頭腦。
・第9屆 新千歲機場國際動畫電影節→日本大獎
・第24屆 長岡獨立電影大賽→大獎
・神戸獨立電影節2022→準優勝
・第31屆 CG動畫大賽→準優秀獎
・第7屆 福井站前短篇電影節→評審團特别獎
・第20屆 上田城下町電影節→評審團獎
・那須短片電影節2022→那須電影委員會獎
獲獎情況大緻如上。獨立電影和商業電影不同,尤其是短片,從制作、完成到電影節上映,節奏異常之快。6月末才完成的電影,突然就入選了各種電影節。我在11月奔赴新千歲、上田、那須、神戶,一下遇到了很多人,從他們那裡直接聽到了對電影的感想。這是我未曾想象過的,思緒也還跟不太上。這一切也太快了……我可是一個在口渴得要命時,會為了要不要去公寓樓前的自動販賣機買果汁而思考上一個小時,最終還是選擇喝自來水的、不愛出家門且讨厭旅行的男人啊。最初一個人上路時,我内心還非常惶恐,腦海中反複回旋着BB QUEENS唱的《第一次跑腿》(はじめてのおつかい)(譯注:一檔讓小朋友獨自出門完成任務的日本綜藝節目)的主題曲,但後面倒是很輕松就克服了。我想着“雖然我喜歡電影,但獨立電影良莠不齊”,所以也沒怎麼好好看其他人的電影,一個人東逛西逛觀光,到小巷深處散步、拍拍照,大吃特吃鄉土料理和當地的精釀,隻出席個頒獎典禮,其他時間都在酒店呼呼大睡……雖然确實有點對不住各方人士,但我自己真是覺得暢快極了。返程時,我腦海中播放的歌曲變成了《威風堂堂》。換句話說,就是快有點得意忘形了。不過說到底,獨立電影這種東西,知道的人寥寥可數,我自己也沒什麼名氣。這種程度根本不可能得意忘形,甚至我自己也還沒有自稱“電影導演”的自信。作為大前提,每個電影節都十分精彩。主辦方東奔西走努力的身姿、對自己的土地和電影的熱愛,我都有看在眼裡,也對此滿懷敬意。每一場活動在我看來都無與倫比。在分别時,工作人員們對我說:“請您明年也來參與。”我在感到喜悅的同時,又有一種心煩意亂之感。這是因為,我是為了從中脫穎而出、離開此地,才向獨立電影節投稿的。所以我今後一定要制作更加不同凡響的作品。對我來說最理想的未來是,在各個電影節的上映影院,以特别放映之名單獨上映我的電影吧。11月我過得眼花缭亂,時間如彈指間流逝。當下,我的心境正如上述。也正因如此,為了在這個階段理清我的思緒,我想着要留下這篇文章。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個原因。在各地上映時,當一期一會的觀衆向我坦率表述電影感想時,我除了“謝謝”以外找不出任何話語回應,這讓我十分懊悔。“你這個認生又嘴笨的假高冷混蛋……再多回點别的啊!”我對自己感到很生氣。因為在那時,我了解到有許多觀衆都很好奇電影的構想和手法,我才想在這裡毫無保留地分享出來。我要大寫特寫一番,讓那些過度解讀的人大失所望。
【關于聲優】
回想起來,我還從未有過和“正經的演員(雖然這麼說會對以往的出演者有點失禮……)”合作的經曆。我讀的是東北藝術工科大學(山形)的映像學部,校内不設一般電影學校都會有的演員課程,所以想拍電影時,通常是請朋友或後輩參與。拍攝場地隻有公寓、公園或大學校内,學校不怎麼給制作經費,演員還都是純素人,學校也不教要怎麼給酬勞,所以基本就是讓他們志願出演……對于想當電影導演的人來說,這環境真的不能算好。不過,通過從零開始指導素人演員的演技,倒讓我學習了不少導演的知識。我在山形拍了幾部真人電影,來到東京後從就職的制作公司逃走,為了尋求刺激的劇本構思來到歌舞伎町後,由于疫情,店鋪歇業,我便就此契機開始制作動畫。第1部作品《MAHOROBA》基本沒有台詞。尾聲部分的一點點台詞,我麻煩的是我的高中同學。所以我就決定,我的下一部作品一定得有滿滿當當的台詞,要做成一部可以和演員密切合作的作品。于是,在《無法的愛》的制作階段,我在Twitter上招募了聲優。盡管我隻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無名導演,招募詳情也寫得樸實無華,但依舊收到了幾十人的申請。我從中選出了2位主要聲優,又為在電影尾聲登場的4位角色增加了4位聲優。接下來,我想詳細記錄一下我們“特殊”的合作方式。
甄選階段,我招募的是“男性”和“女性”的聲優,為兩者各自準備了考核台詞。我記得應該是“我想做善事~”和“我故意走偏了人生~”這兩段。我讓申請者通過Twitter的私信把台詞的錄音發給我。從中,我最後敲定男性角色(隻野一男)由巴山祐樹先生,女性角色(愛)由小林桃香女士擔任。申請者中很多人從事的是動畫聲優或旁白的工作,而我了解後發現,巴山先生和小林女士,兩位都主要作為電影和舞台劇演員活動。其實我并非一開始就想找演員做聲優,完全是聽聲音決定的,但這兩位身上有一個共同點——相較其他人,情緒都非常低沉。我這部動畫和其他所謂的日本動畫不同,在我的設想中,隻希望聲音平平淡淡,并不需要誇張大膽的情感表現。我在招募階段其實并未明确說明這一點,但也是想着如果申請者看着考核台詞和角色插圖,就能靠自己的判斷,給出與我構想相近的聲音質感,這樣的申請者才是最合适的,所以最後敲定了這2位。後面我們通過ZOOM進行了第一次面對面交流。交流中,我發現兩位都是第一次挑戰用聲音表演,我不知怎麼地也安心了。再之後,兩位還特地來到我工作的危險地帶——歌舞伎町的酒吧,我們在那兒又聊了許多。回想起來這流程也是非常離譜,那時我幾乎還沒動筆寫任何台詞,隻有畫在一張張畫着。而且也隻是在“這裡可能要說個台詞吧…”的地方,提前留下嘴部開合的畫面,就放在一邊了。這也是因為這部作品雖然有台詞,但我最開始設想的就是基本按獨白的形式講述,所以覺得總歸到時候會有解決辦法的……我那個時候應該也是想逼自己一把吧,所以才在台詞都八字沒一撇的時候,想着先把聲優确定下來。1個人制作作品,其實是非常孤獨的,而且又不算是工作,一個不小心就可能一直偷懶下去。對當時的我來說,我很需要一個推着我往前走的壓力,所以2位聲優的到來對我的幫助相當大。
我并不了解慣常的動畫制作現場是怎樣的,但根據紀錄片裡展現的流程,錄音基本上都是“後期配音”。可是正如前述,我這部作品的制作風格是邊畫邊想大緻台詞,沒辦法進錄音棚配音,我自己也不太希望這樣。比如說,就算我準備好了所有的台詞一次性全錄完,我知道我自己肯定第二天一起來又會想“那裡好像不太對……”。所以我想出來的辦法是——“在Amazon上買麥克風送到他們家,分次慢慢錄音”。如此,不僅可以遠程錄音,而且還能反複做細微的修改。就是麻煩了巴山先生,他家離車站比較近,為了避免電車噪音,不得不在深夜錄音……真是非常抱歉讓您在大半夜用超大音量喊“把我的自行車還給我~!!”。
實際上,在加入聲音後,劇情設計上也做了很大的變動——我讓死去的愛擔任了後半部分的旁白。最初的設想是全篇隻有隻野的獨白。但小林女士的聲音質感太好了,不讓她多說幾句覺得太過可惜,同時又覺得讓死去的人說話也不是不行,就做了更改。現在看來是個不錯的決定。此外,在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制作的過程中,到收尾階段,突然發現需要再追加4位聲優。正當我想着“糟了,怎麼辦……”焦頭爛額的時候,我重新聽了甄選時落選的各位的錄音,從中又厚臉皮地選了4位,請他們擔任非主要角色的聲優。與隻野對峙的“無名無差别殺人犯”由大門嵩先生,渾身顫抖的“路人男”由Tommy(我的大學同學),台詞量比主人公還多的“新聞主播”由KUREHA先生,把賠笑體現得淋漓盡緻的“女主播”由彼方女士擔任。各位的表演都十分出色,我深表感謝。
【關于音樂】
動畫全篇畫完之後,我才終于進入了搜集音樂的工序中。環境音和效果音,我是找了大概4家免費網站才收集完。說實話,真的挺麻煩。但根據我的經驗,如果在這些音效上犯懶,就會把獨立電影的格調降至2流3流之下,所以必須下功夫讓音效至少在合格線以上。與此同時,我也開始制作樂曲。制作《MAHAROBA》時,我用的是一個叫作MUSICBED的、可以使用免版稅樂曲的訂閱收費制海外網站。我在上面搜羅了一堆樂曲。但在著作權上無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灰色地帶,比如“這首歌不能在某個國家使用”等等,我為此勞心傷神了很多次,所以想着在這部作品中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這些年,說着“日本電影很無趣”的聲音愈發多了起來。我認為原因之一就在于電影使用的音樂。商業電影一般就是找個根本無人知曉的土氣樂隊,讓他們寫首新歌,然後在片尾放一放。獨立電影也不咋地,當令人感動的一幕出現時,仿佛在跟你說“就是這兒了,感動起來吧”一樣,一定要放首鋼琴曲在那裡哒啦啦啦,而片尾滾動時,又仿佛就是為了讓你聽那首糞曲,沒幾個人的演職人員名單在那裡很慢很慢地滾。還有的電影,導演完全逃避使用音樂,不知道是不是他喜歡法國還是哪裡的電影,完全自我沉醉其中,說什麼自己拍的是“長鏡頭”,整部電影完全靜音,搞得像在看星象儀一樣,讓人看着看着就美美進入夢鄉……對不起我語氣有點亂了,但我一直以來确實都挺納悶,會想“難道就沒有音樂恰如其分的電影嗎!”。我自己想和那樣的電影劃清界限,打算在電影各處使用音樂,為電影的節奏加壓,也想給畫面帶來韻律感。這時我正好發現了一個名為“splice”的采樣音源網站。
splice是一個說唱歌手和音樂制作人等專業領域的人士也都在使用的訂閱制網站,上面分開售賣着數以萬計的節拍和旋律。我從中下載了自己所喜歡的樂曲,(我自己是)用GarageBand(譯注:蘋果公司編寫的音樂創作軟件)将其組合到一起。“把其他人制作的元素組合到一起,就成了自己的”。這種樂曲制作方式和我制作動畫的感覺非常接近。要說的話,這也是一種“無數抄襲”的集合體。這次我本就打算讓這部作品的音樂更具嘻哈感,所以能找到這個網站,可以說是這回最大的收獲。在樂曲的氛圍營造方面,我比較注意的是前後部分的切換。前半比較明朗,主要運用的是經典節拍,後半則往黑暗低沉的方向調整。尤其是制作後半部分的樂曲時,我聽了大量KOHH和NIRVANA的作品作為參考。在制作動畫時也好,制作音樂時也罷,我經常會根據自己的興緻,在對使用方法毫不了解的情況下開展工作。所以着手下一部電影時,我希望能再提前多學習了解一些。
【尾聲】
至此,像是殺人犯在接受調查時細細講述自己的殺人經過一樣,我随着自己的興緻洋洋灑灑寫了一堆,但我能談的大概就是以上這些了吧。閱讀完這些文字所要的時間,或許比《無法的愛》本身的時長還要長。認真讀到這裡的人,等之後再見到我時,可能已經沒什麼想再跟我說的了吧……
看完電影後,在Filmarks寫下評論,再看其他人留下的評論……不禁讓我覺得,觀衆可真是不管不顧且殘酷啊。或許也出于這個原因,在制作電影時,我總是一邊自嘲着“根本就沒人認識你”,一邊淡淡地推進作業。不過這麼回顧一番制作過程,期間倒的确經曆了不少事,也再次感到身為電影人理所應當就是要動這麼多腦筋的吧。世上沒有正确答案,但錯誤是存在的。我不想犯錯,也不想制作無用的電影。我要變得更加孤獨,制作出更為出色的作品。我要過上希求“做出色作品”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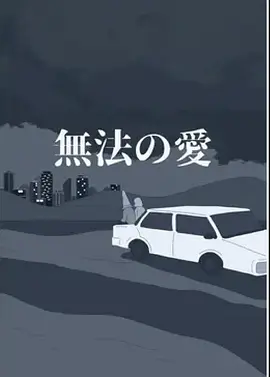

![[MIDE-742] 高橋聖子 2020 最新騎兵作品](https://upload-images.jianshu.io/upload_images/20131127-7d8d281d5f1cd953.jp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imageView2/1/w/300/h/240/forma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