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极 限 审 判》:犯 罪 档 案 的 “重 写” 技 艺 与 疑 案 诗 学 - 微信公众平台】
《极限审判》是俄罗斯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Timur Bekmahambetov)执导的一部人工智能题材科幻电影。电影讲述了雷文警探因被污蔑以谋杀罪,而被置于人工智能法庭之上。他必须在90分钟内,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完成清白自证,否则就会被执行死刑。在电影主题层面,《极限审判》作为一部探讨人工智能及未来人类科技化生存状态的科幻电影,其思想深度并没有显著突破,仍停留在拾取科幻经典的思想碎片水平上。但若将本片置于“桌面电影”(Desktop Film)的创作序列,那么将疑案诗学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叙述尝试,则为此类电影创作提供了叙述学维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贝克曼贝托夫一直对“科技-叙述”的可能性保持着探索热情,其担任制片人的多部作品,如《解除好友》(Unfriended,2014)、《网络谜踪》(Searching,2018),及其续作《网络谜踪2》(Missing,2023),均围绕网络空间的犯罪故事展开。其中,《网络谜踪》作为2018年的现象级“黑马”之作,曾一度让“桌面电影”概念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在《极限审判》中,“桌面叙事”的形式特征得以保留,并且得益于科幻题材缘故,影片中的“桌面”设定也被赋予了超现实性,传统电脑桌面迭代为“无边幕布”的沉浸式存在。然而,在科技设定上超越传统“桌面电影”的同时,《极限审判》也触及到这一电影模式的叙述转型,即从对存储电子文档的考古学,转向对生成式数字档案的动态叙述。
 网络谜踪 (2018)8.52018 / 美国 俄罗斯 / 剧情 悬疑 惊悚 犯罪 / 阿尼什·查甘蒂 / 约翰·赵 米切尔·拉网络谜踪将“桌面电影”的概念与制作推向热潮
网络谜踪 (2018)8.52018 / 美国 俄罗斯 / 剧情 悬疑 惊悚 犯罪 / 阿尼什·查甘蒂 / 约翰·赵 米切尔·拉网络谜踪将“桌面电影”的概念与制作推向热潮
回顾开篇人工智能法庭宣传广告的结语:“您已被分配的案件编号为19。”这宣告着,雷文警探在电影叙述的伊始阶段,就被置于一份已由人工智能法官“撰写”完毕的犯罪档案之中。其立案依据,是人工智能根据云端数据库中的碎片化影像,组构出的“犯罪控诉”。对于这一朝向死亡的“犯罪控诉”,雷文警探必须借助人工智能赋予的能力,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档案的“无罪辩护”。于是,封闭的“犯罪控诉”与依托流动数据开展的“无罪辩护”,构成了整部电影叙述的底层逻辑。
一、“犯罪控诉”与“无罪辩护”的话语冲突
在日常语境中,“档案”通常被理解为“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分类保存的各种文件材料”。然而,档案的制作常蕴含着一个叙述学悖论:档案所记录的主体,其档案内的材料叙述永远是由他者书写。换言之,档案作为官方对个体的认证,在其零散材料的叙述转化过程中,剔除了个体进行自我叙述与辩护的权力。这种源于他者书写的个体叙述困境,构成了“犯罪档案重写”这一经典疑案模型的核心背景,这也是《极限审判》的故事模型。
在“犯罪档案重写”的叙述中,被误判的“罪犯”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一个由官方机构建构的“犯罪控诉”。在《极限审判》开篇,马克多斯法官打开一个名为“证据文档”(Evidence Files)的文件夹,其中包含着众多视频文档。通过串联交通监控、居家摄像头、酒馆录像、执法记录仪、新闻片段等一系列碎片化资料影像,马克多斯法官将之组合为一个逻辑缜密的“犯罪控诉”。该控诉在银幕上呈现为一个封闭的过去完成时态空间,其效用建立在记录式影像的客观性之上。面对已然凝固的叙述空间,雷文警探的辩护必须克服双重叙述困难:其一,他必须寻找在证明力度上超越既有档案影像的新材料,以实现有效驳斥;其二,寻找新材料的目的,不是简单否定既有档案资料的真实性,而是必须在涵盖原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叙述扩展。可见,“犯罪档案重写”的本质,是在同一套叙述材料上,展开“犯罪控诉”与“无罪辩护”两套话语间的竞争。
作为一部人工智能题材的科幻电影,《极限审判》提升了“无罪辩护”的难度,主人公不能求助于律师这样的传统角色。在这部电影构建的乌托邦中,律师的辩护与逆转功能,让渡给了被雷文警探和人工智能系统。这一设定具有双重效用:消极一面是,这几乎等于一开始就预设了主人公的无辜,自动放弃一种剧情翻转的可能。积极的一面是,当翻案的希望完全系于被告自身时,叙述便自然地将观众注意力聚焦在主人公的自证过程上。而后者正是该片基于人工智能题材创新的核心看点。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档案重写”应当从何入手,才能显示出科幻题材的陌异化特质?《极限审判》中犯罪档案的科幻化,最直接体现在它的数字本体上,它排斥带有主观色彩的个体叙述作为证据,仅接受被媒介中介化后的信息。于是,简单的口述被排除在了有效的“无罪辩护”之外。正如影片结尾处,马克多斯法官建议真正罪犯罗伯提供有效证据,通过官方渠道来解除对他弟弟的有罪指控,而罗伯的即时口述在可视知觉罪证前显得漏洞百出。
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档案重写”需要一种新档案书写技艺,它在形式上可被概括为跨媒介与数字化,在叙述学上则可称为“广义叙述”。按照傅修延的说法,人类是以叙述为生的“叙事人”(Hommo narrativus) 。但人工智能时代不仅需要叙述的本能,还需具备跨媒介非线性境况下的线性叙述能力。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提出过两种“跨媒介叙述学”(transmedial narratology):一种是可分为面对面叙述、单幅画叙述、电影、音乐、数字;另一种则依据讲述模式、模仿模式、参与模式、模拟模式来进行划分。赵毅衡认为瑞安的分类法,虽强调了跨媒介,却忽视了文字。于是,他从文字这种人类历史上最核心的叙述媒介出发,提出能讨论所有叙述体裁的共同规律的“广义叙述学”。因为涵盖所有叙述体裁,那么自然也囊括了所有具有叙述能力的媒介,包括记录类(文字、言语、图像、雕塑),记录演示类(胶卷、数字录制),演示类(心像、心感、心语)、意动类(任何媒介)。
在此视域下,可以勾勒出《极限审判》中雷文警探所处的“广义叙述”状态。其叙述行为的物质性载体,是对城市中不同规格信号里可视化材料的汇集与调取。当影片中的“人工智能法庭”被官方认证为一种城市基础设施时,它拥有了超级技术系统协议的权限,即能够访问媒介的云端存档。由此引出的是一个由低空飞行网络、无人机、城市监控构成的实时影像网络。这些即时影像组合成的新叙述框架,因其进行时态,而有力地覆盖了过去完成时态的犯罪控诉。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曾洞察数字档案的流动,他指出:“在互联网的案例中,档案基础设施只是暂时的,以回应永久的动态重写。终极知识(旧的百科全书模式),让位于永久重写或添加原则(维基百科)。” 这种永处进行时态的生成性法则,渗透进未来的犯罪档案学,只要档案主体拥有足够的自证资料与自洽逻辑,都能进行有效的无罪辩护。
 极限审判 (2026)7.52026 / 美国 / 动作 科幻 悬疑 / 提莫·贝克曼贝托夫 / 克里斯·帕拉特 丽贝卡·弗格森
极限审判 (2026)7.52026 / 美国 / 动作 科幻 悬疑 / 提莫·贝克曼贝托夫 / 克里斯·帕拉特 丽贝卡·弗格森
当然,导演会在“犯罪档案重写”过程中增添阻力。影片过半之际,尽管雷文发现了新线索与嫌疑人,但是他的犯罪系数却变得更高。人工智能作为信息选择者,它有权力评判哪些信息可以进入档案,覆盖原有叙述,而哪些信息又需要被排除在档案外。其筛选标准,正是台词所强调的证据间“线性思考”。这预示着在广义叙述时代,人类不仅要有信息发现能力,还需具备将非线性、碎片化的材料,转化为具有因果逻辑的线性叙述能力。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档案重写”,还强调一种类似剪辑师所擅长的多模态信息整合和叙述能力。有别于蒙太奇追求的意义生成,这种能力的目的是在纷繁材料中实现清晰叙述。
二、人工智能法庭上还有“疑案”吗?
借助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经典设问——“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或许可对《极限审判》中的未来司法图景提出一个类似问题:在人工智能法庭上,还会存在“疑案”吗?按照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普遍期待,其毫秒间的信息整合和逻辑推演能力,理应避免疑案产生。马克多斯法官的台词解释了这种逻辑,她说:“你正追随直觉行事,但处理证据需要清晰线性的思考。你必须从谜题的一块逐步推进到下一块……”人工智能法庭呈现出一种符号主义(symbolism),或可称之为逻辑主义(logicism) 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信息拾取,即将每个可视证据都被转化为可供读解的符号文本;其次是推理运算,通过寻找不同符号间的递进逻辑,实现组合轴操作,以此叙述逻辑统摄零散证据;最后,输出一个逻辑自洽、无可反驳的犯罪故事。当犯罪证据趋于饱和时(正如一个镜头中的雷文被淹没在有罪的信息海洋中),依据此思维方式生成的“思维链”就会相当严密。理论上,一个能接入全域数据的人工智能法庭,确有可能消除“疑案”产生。
《极限审判》的思想实验在于,它指出即便将碎片化的可视证据组合为逻辑高度自洽的叙述空间,但其内部仍会存在断裂缝隙。“有罪控诉”的空间贯连不等于事件本身,它以逻辑推论的动力和诱惑,掩盖了不同媒介影像的剪辑接合面。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符号”的空白,蕴含着真相本身。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指出:“‘数字记忆’的问题已经不是‘再现’问题,而是如何以记忆的算法技术本体论进行思考的问题。” 影片中的人工智能法庭显然仅相信可视证据的再现,以及再现与再现间的逻辑衔接。雷文所作出的“直觉式”推论,是被迫从组合轴元素上抽离,而回到蕴含丰富可能的聚合选项中。雷文进行的一系列侦探行为,包括:对女儿社交媒体片段的读取、尼科尔手机通信录人员信息的读取、尼科尔手机摄影片段的读取等,全是重新激活聚合轴选择的做法。
 走向媒介本体论:欧美媒介理论文选8.7韩晓强 主编 / 2024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走向媒介本体论:欧美媒介理论文选8.7韩晓强 主编 / 2024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重回聚合轴选择,对人工智能题材下的“犯罪档案重写”有着双重意义。从内容层面来说,重回聚合轴意味着重回证据“星丛”。将人工智能确定的有罪控诉“重写”为无罪辩护,首要步骤是将案件的“确证状态”还原为“疑案状态”。从科幻思想层面来说,雷文通过人脑推翻人工智能的有罪推论,暗示着一种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正在生成。电影将这种“高级”智能神圣化为“人的直觉”,其本质就是在聚合轴选择中,接受多重叙述生成,并进行合理性对比的能力。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指出:“大型神经网络学习语言,不需要任何先天结构,只是从随机权重和大量数据中开始学习……乔姆斯基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种有关语义(semantics)的理论,他的理论全是关于句法(syntax)的。” 《极限审判》中的人工智能实则是复现了一个古早的“逻辑主义”人工智能,它虽体现出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的极致强化,但却因阉割聚合轴选择能力,丧失了涌现功能。因此,有影评指出《极限审判》中的人工智能不够聪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单是因为电影以人工智能法庭的误判作为开始,还在于她本身对聚合轴选择能力的阉割和让渡,使之以人类智能的方式出现。一种偏戏谑的说法,《极限审判》中“疑案”生成的原因之一,是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只是用数字特效装饰了的早期版本。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评价人数不足赵毅衡 / 2025 /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评价人数不足赵毅衡 / 2025 / 四川大学出版社
当然,即便是《极限审判》中“疑案”的游戏过程并未达预期中的精妙。但仅就其营造的“疑案”风味来说,电影仍是合格的。这种弥漫于“犯罪档案重写”过程中的独特质感,笔者认为不能称之为技法,而是“桌面电影”这一形式影像材质的特性。学者韩晓强曾对“桌面电影”的叙述形式进行总,触及到以下叙述学内容:其一,“桌面电影”依靠各种智能摄像头的“拾获影像”进行叙述;其二,“桌面电影”依赖操作系统和媒体软件推进情节;其三,叙事载体限制在智能屏幕桌面内,依靠光标叙事和窗口叙事两种模式;其四,采用主观视角,所有交流通过打字或视频呈现,主角和观众知道的信息一般。 文章认为,以上总结的共性在于,均揭示了“桌面电影”的影像材质都处于一种过去式完成时态。每一个被调取的存储影像,都是对已发生之事的回溯,即倒叙。譬如,人工智能重建的现场运动轨迹、DV记录的聚会片段,包括可视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是指示了一种过去已经发生的链接。“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构成了碎片式的倒叙迷宫。在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的疑案叙述考古研究中,意在言说过完之事的倒叙手法,在194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电影中就已经成为相当通俗的叙述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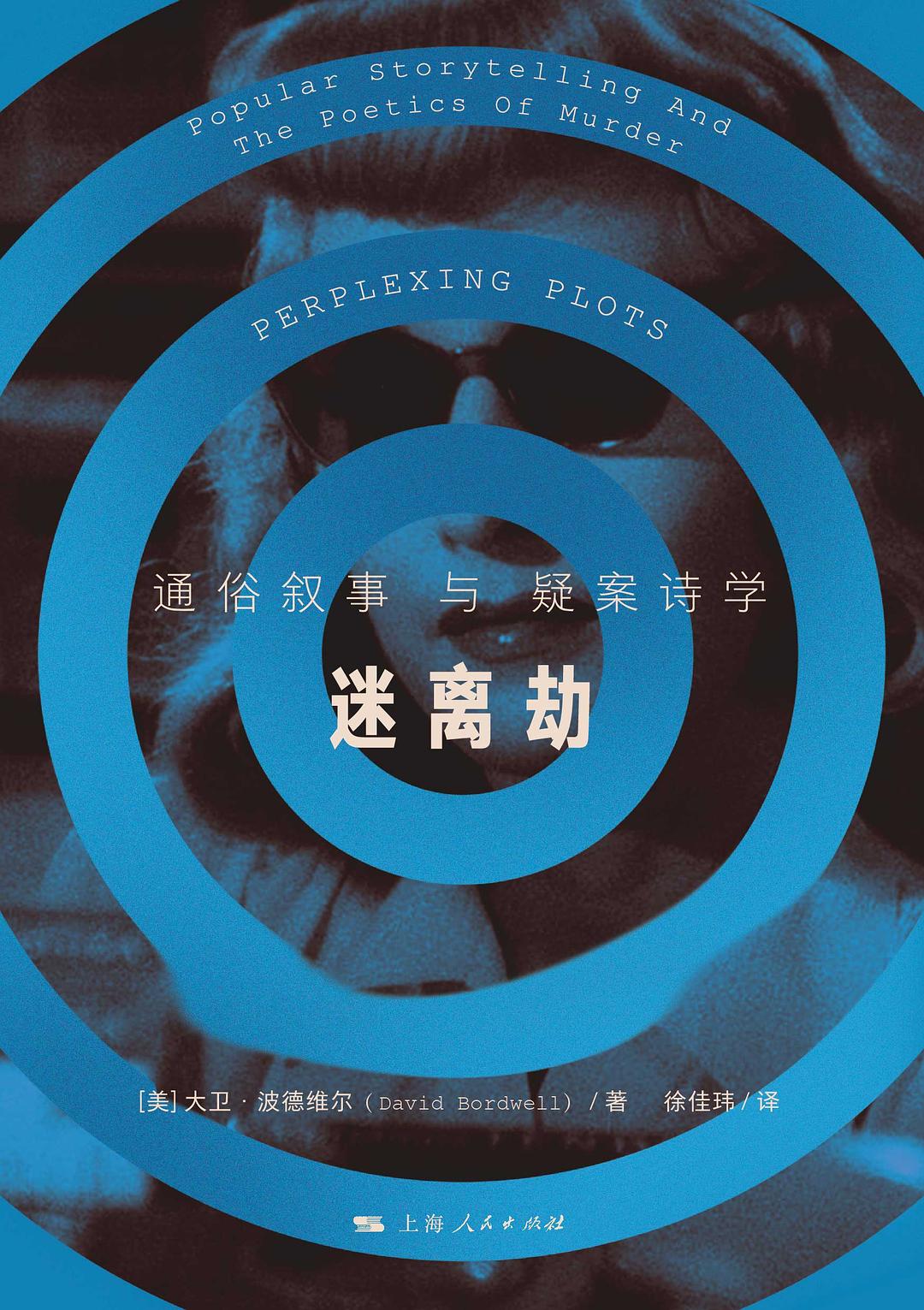 迷离劫9.2[美] 大卫·波德维尔 / 2025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迷离劫9.2[美] 大卫·波德维尔 / 2025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极限审判》中提升“疑案”风味的另一策略,是对雷文警探行动能力的彻底限制。他被固定一张装有声波装置上的审判椅上,倒计时结束就会触发声波而亡。在疑案诗学的叙述传统中,身体受限与思维灵动的二元设定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从奥西兹(Baroness Orczy)笔下仅凭报纸新闻就能推演迷案的“角落老人”,到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塑造的不爱走动却擅长推理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再到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作品中体重超常、仅依靠助手获取案件信息来推论的侦探沃尔夫。这一系列通俗叙述中的侦探形象,被统称为“安乐椅神探” 。《极限审判》中的雷文显然是可以置于在这一形象脉络上。值得追问的是,《极限审判》是真正地塑造了一位2029年的“安乐椅神探”,还是仅仅巧妙借用了“去身体”的探案模式,转而跃入“无身体”的信息全知视角中。回答此问题,需要再审视该片中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影像——“即时影像”。《极限审判》中的即时影像主要呈现为有三种:手机可视通话、电脑即时通讯、监控摄像头的实时流。这些即时影像是雷文在“安乐椅”上追捕凶手的关键工具,但是电影对它们的无限制启用,打破了“桌面电影”的一个重要形式原则,即对屏幕内空间的不可干预性。电影中,迪亚洛警官随时保持着与雷文的通讯,依照其指示,驾驶空中不断地摩托穿梭在城市之间。雷文放弃行动,却有着调用整个城市人力与可视基础设施的能力。导演巧妙地为“疑案”设置了一个身体性难题,但他并没有打算用传统方式来破解难题,转而通过人工智能这把“万能钥匙”赋予了侦探以全知视野。
 角落里的老人7.6(英)奥希兹女男爵 埃穆什考·欧尔齐男爵夫人 / 1999 / 四川人民出版社
角落里的老人7.6(英)奥希兹女男爵 埃穆什考·欧尔齐男爵夫人 / 1999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结语:科技想象升维与叙述技艺降维的矛盾
《极限审判》确实在故事传统、叙述设定与叙述技巧上,为“疑案”制作铺设了充分条件。然而,从互联网平台的广泛评论来看,电影的“悬案”质感却远不及预期,甚至与同为“桌面电影”序列的《网络谜踪》来说,其悬疑张力也是逊色不少。导演极力铺陈的谜题,在人工智能赋予的几近全知叙述视角下,轻易地消解了“疑案”技巧的叙述视角限制。因此,影片中科技的想象升维,与随之发生的叙述技巧降维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矛盾。
从《网络谜踪》到《极限审判》,“桌面电影”在影像调用上的复杂化,揭示出一个问题:作为该类电影核心的“桌面”,其媒介特性构成了叙述展开的“双刃剑”——它既是谜面,又是解谜的钥匙。“桌面电影”想要具备足够的悬疑张力,就要足够聚焦在“桌面”之内,而尽可能摒除桌面外的现实干扰。在屏幕的方寸间,做大谜面的广度与深度,而保留那个细小的“钥匙孔”。但当创作力不足以支撑起心智游戏时,一种退而求次的做法就是让“钥匙孔”变大。《极限审判》正属于后者。同为对“拾获影像”的组合轴操作,《网络谜踪》因只能现实主义手法限制,其技术被锚定在对旧数据库的调取维度。主角如同传统侦探,在有限的信息碎片中进行层层发掘。而《极限审判》的人工智能跨越,逃脱了这种经典的回溯模式,将故事推推入到一个更广义、更即时的未来维度。技术赋能与电影叙述技艺的进步没有必然联系,人工智能提供的全域化叙述视角,在丰富视觉体验的同时,也消磨了“桌面电影”原有的悬疑诗学模式,最终让《极限审判》走向了一部“爆米花”之作。
 广义叙述学9.0赵毅衡 / 2013 / 四川大学出版社
广义叙述学9.0赵毅衡 / 2013 / 四川大学出版社
![[MIDE-742] 高桥圣子 2020 最新骑兵作品](https://upload-images.jianshu.io/upload_images/20131127-7d8d281d5f1cd953.jp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imageView2/1/w/300/h/240/format/webp)

